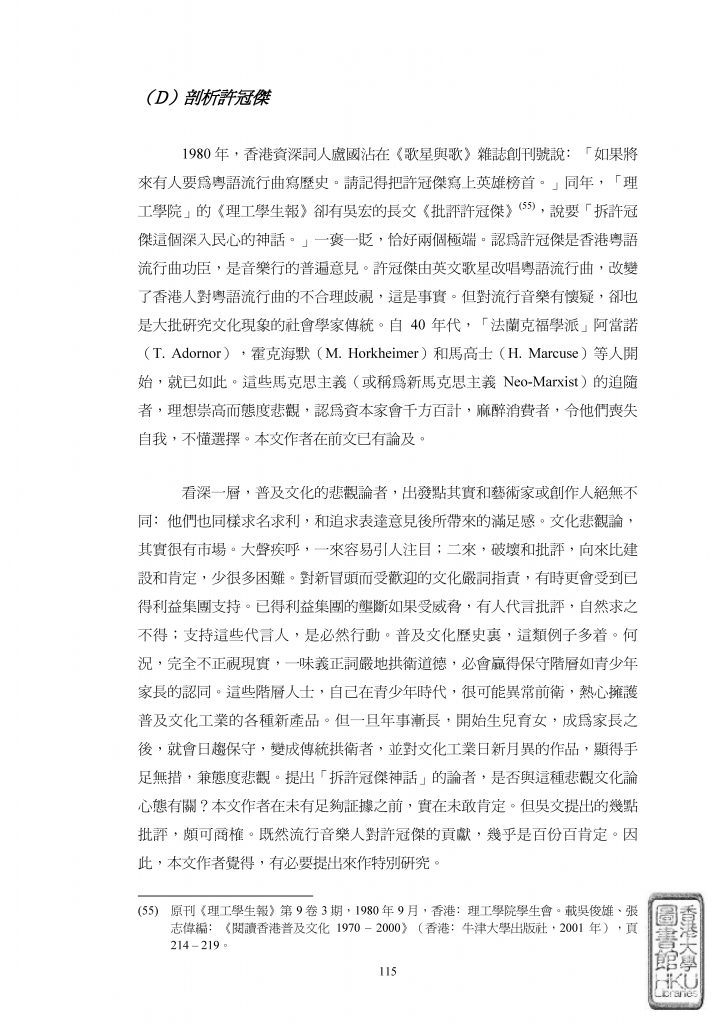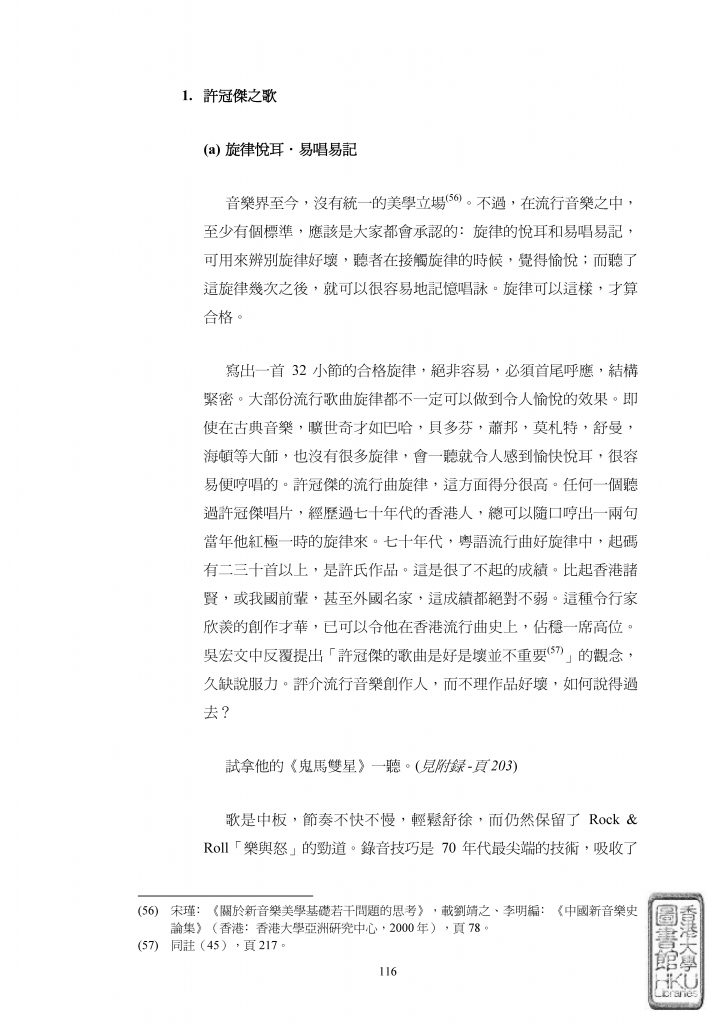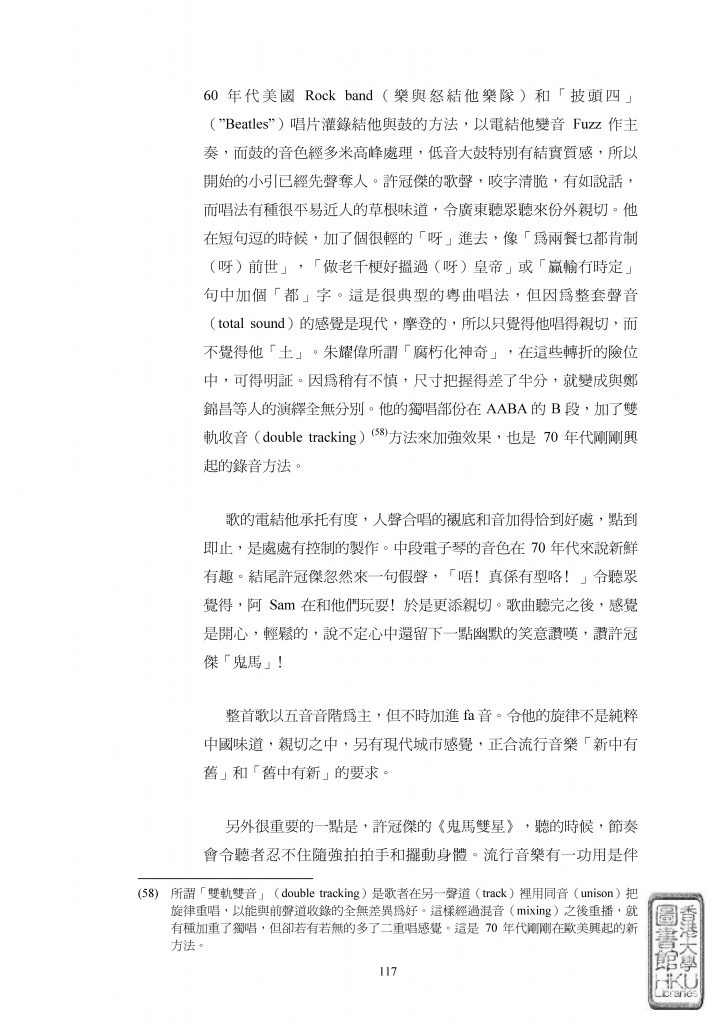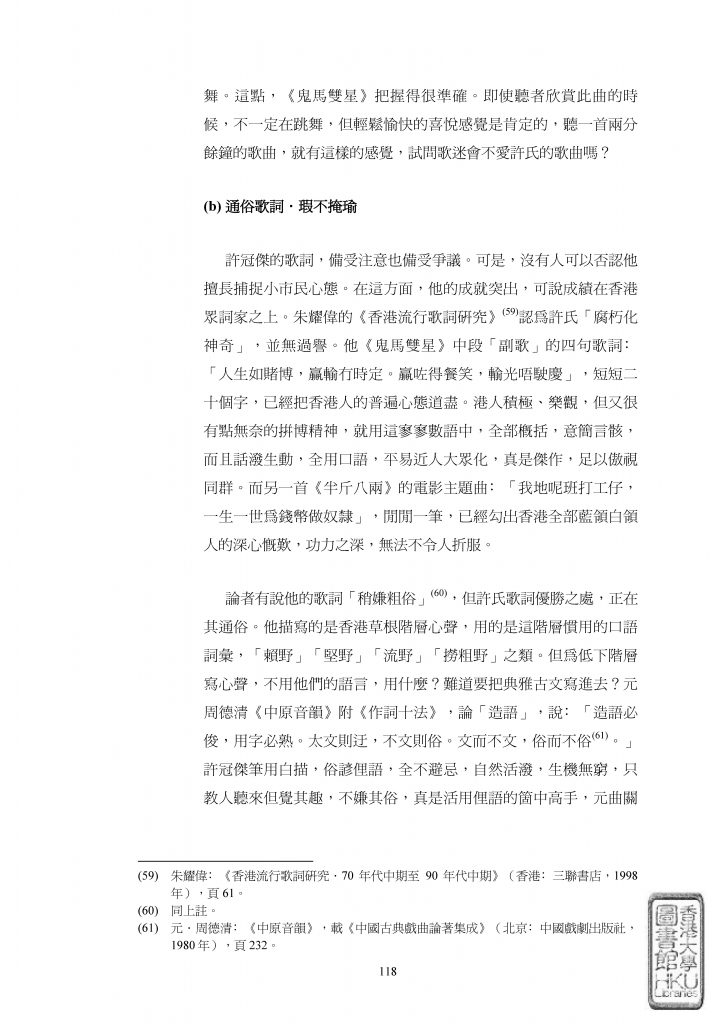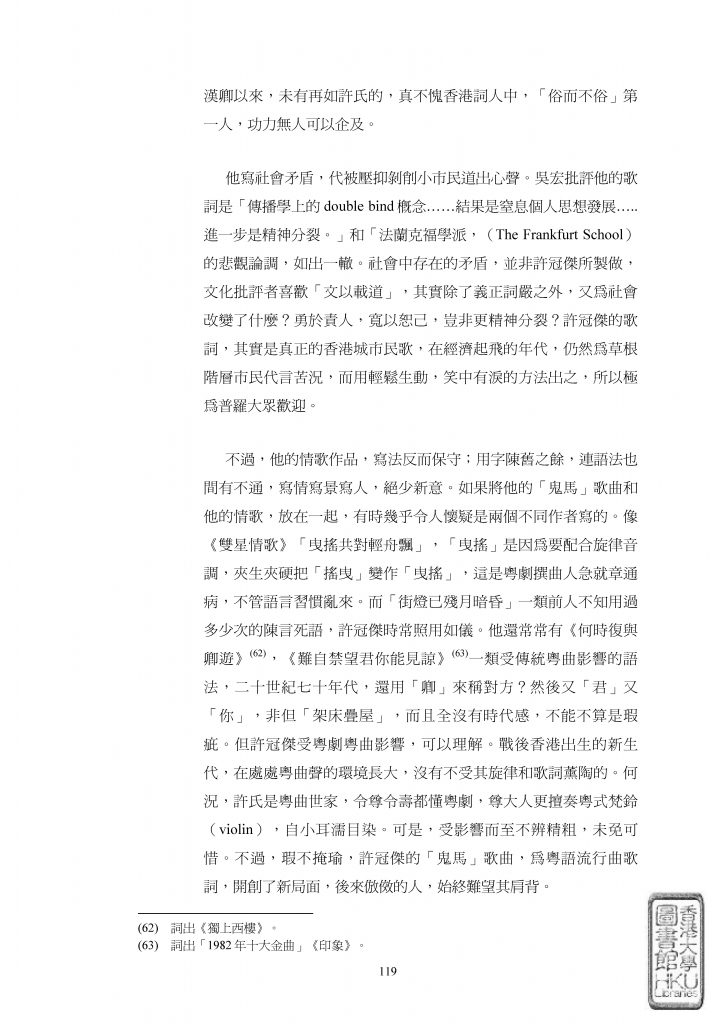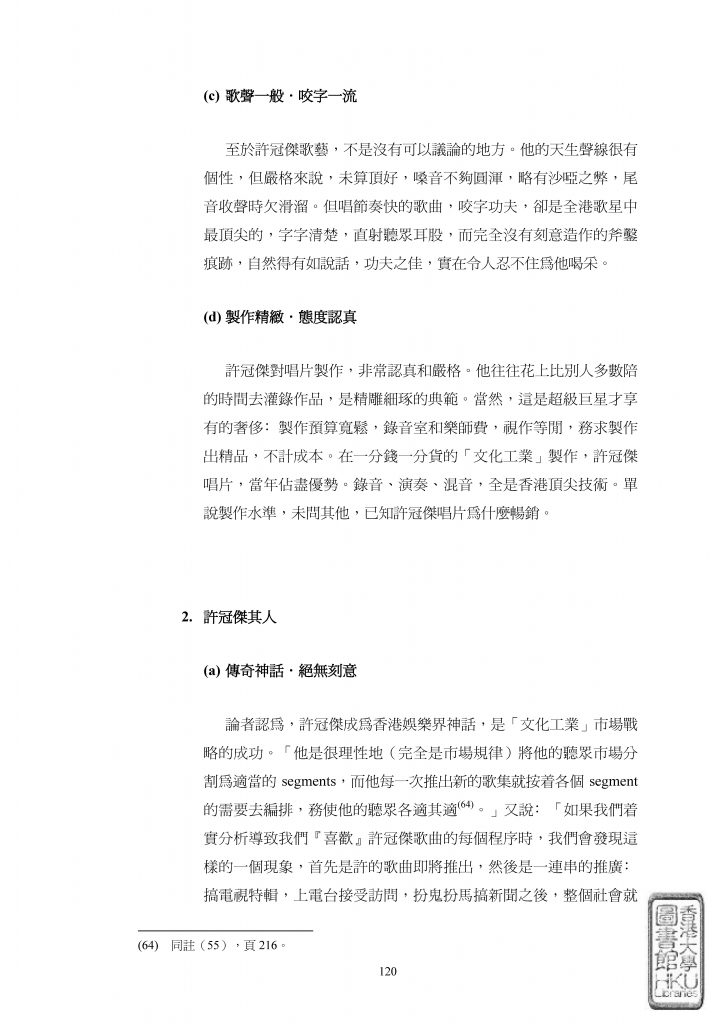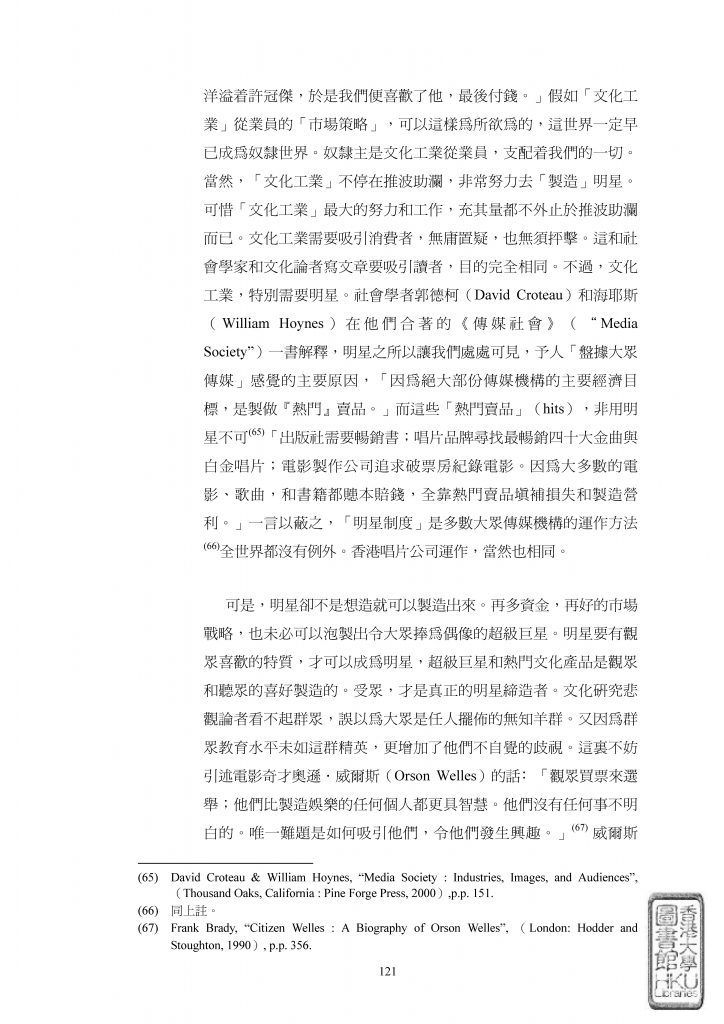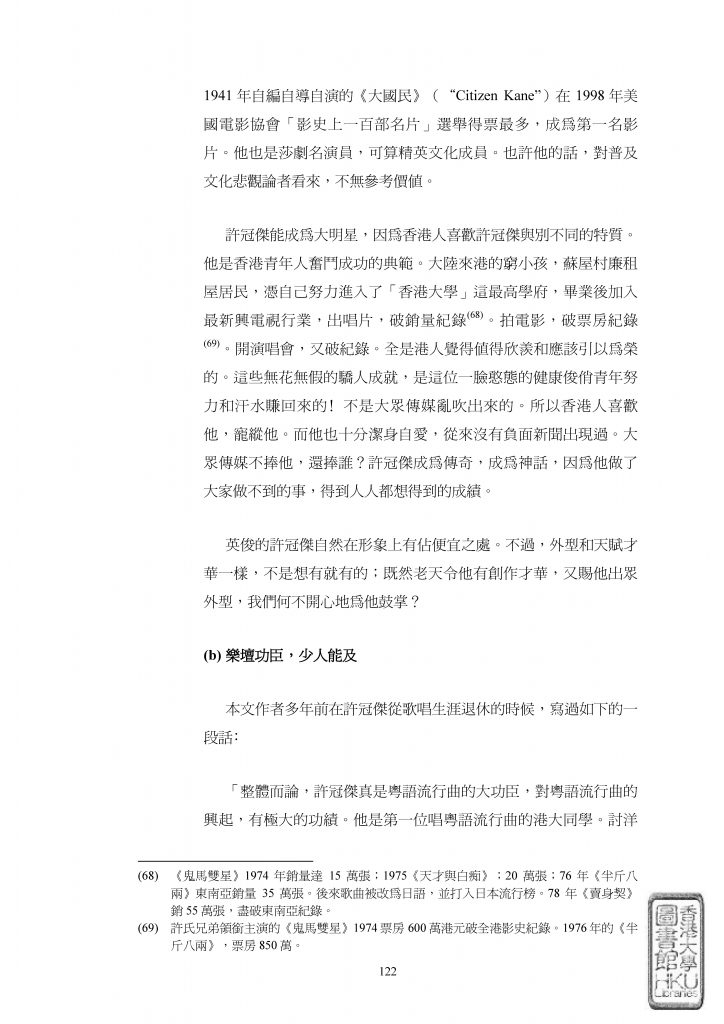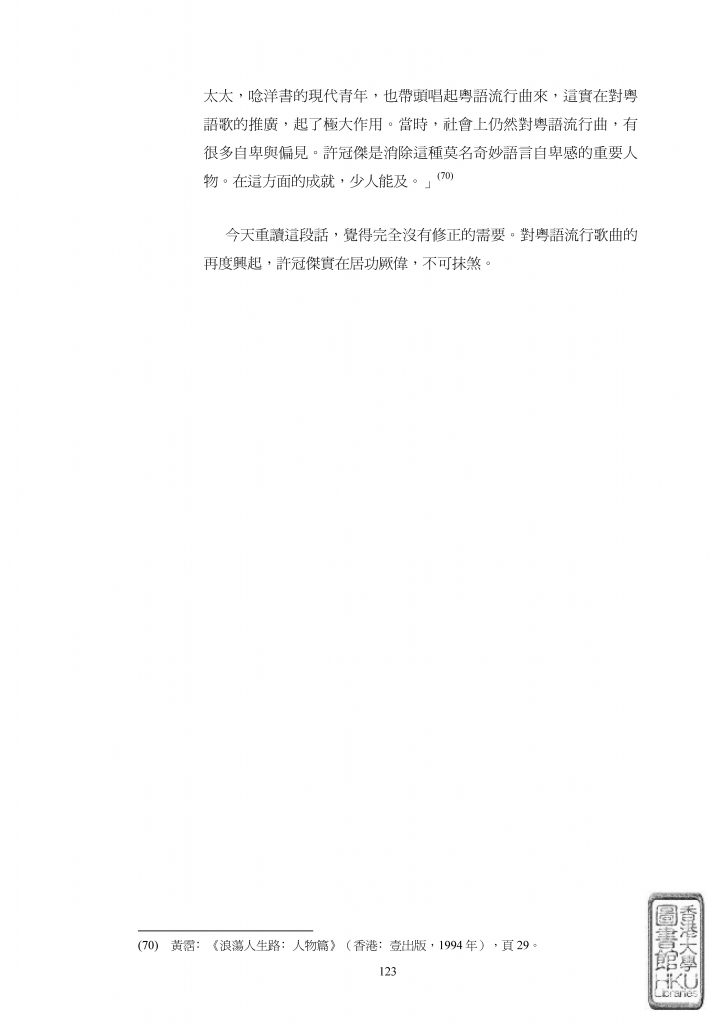咁多人寫許冠傑,最能剖析許冠傑是黃霑吧!
(附論文掃瞄檔)
黃霑:
1)許冠傑之歌:旋律悅耳.易唱易記;通俗歌詞.瑕不掩瑜;歌聲一般.咬字一流;製作精緻.態度認真⋯⋯
2)許冠傑其人:傳奇神話.絕無刻意;樂壇功臣,少人能及⋯⋯
【剖析許冠傑】
(黃霑:《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:香港流行音樂》,博士學位論文,頁115-123)

1980 年,香港資深詞人盧國沾在《歌星與歌》雜誌創刊號說﹕「如果將來有人要為粵語流行曲寫歷史。請記得把許冠傑寫上英雄榜首。」同年,「理工學院」的《理工學生報》卻有吳宏的長文《批評許冠傑》(55),說要「拆許冠傑這個深入民心的神話。」一褒一貶,恰好兩個極端。認為許冠傑是香港粵語流行曲功臣,是音樂行的普遍意見。許冠傑由英文歌星改唱粵語流行曲,改變了香港人對粵語流行曲的不合理歧視,這是事實。但對流行音樂有懷疑,卻也是大批研究文化現象的社會學家傳統。自 40 年代,「法蘭克福學派」阿當諾(T. Adornor),霍克海默(M. Horkheimer)和馬高士(H. Marcuse)等人開始,就已如此。這些馬克思主義(或稱為新馬克思主義Neo-Marxist)的追隨者,理想崇高而態度悲觀,認為資本家會千方百計,麻醉消費者,令他們喪失自我,不懂選擇。本文作者在前文已有論及。
看深一層,普及文化的悲觀論者,出發點其實和藝術家或創作人絕無不同﹕他們也同樣求名求利,和追求表達意見後所帶來的滿足感。文化悲觀論,其實很有市場。大聲疾呼,一來容易引人注目;二來,破壞和批評,向來比建設和肯定,少很多困難。對新冒頭而受歡迎的文化嚴詞指責,有時更會受到已得利益集團支持。已得利益集團的壟斷如果受威脅,有人代言批評,自然求之不得;支持這些代言人,是必然行動。普及文化歷史裏,這類例子多着。何況,完全不正視現實,一味義正詞嚴地拱衛道德,必會贏得保守階層如青少年家長的認同。這些階層人士,自己在青少年時代,很可能異常前衛,熱心擁護普及文化工業的各種新產品。但一旦年事漸長,開始生兒育女,成為家長之後,就會日趨保守,變成傳統拱衛者,並對文化工業日新月異的作品,顯得手足無措,兼態度悲觀。提出「拆許冠傑神話」的論者,是否與這種悲觀文化論心態有關?本文作者在未有足夠証據之前,實在未敢肯定。但吳文提出的幾點批評,頗可商榷。既然流行音樂人對許冠傑的貢獻,幾乎是百份百肯定。因此,本文作者覺得,有必要提出來作特別研究。
1. 許冠傑之歌
(a) 旋律悅耳.易唱易記
音樂界至今,沒有統一的美學立場(56)。不過,在流行音樂之中,至少有個標準,應該是大家都會承認的﹕旋律的悅耳和易唱易記,可用來辨別旋律好壞,聽者在接觸旋律的時候,覺得愉悅;而聽了這旋律幾次之後,就可以很容易地記憶唱詠。旋律可以這樣,才算合格。
寫出一首 32 小節的合格旋律,絕非容易,必須首尾呼應,結構緊密。大部份流行歌曲旋律都不一定可以做到令人愉悅的效果。即使在古典音樂,曠世奇才如巴哈,貝多芬,蕭邦,莫札特,舒曼,海頓等大師,也沒有很多旋律,會一聽就令人感到愉快悅耳,很容易便哼唱的。許冠傑的流行曲旋律,這方面得分很高。任何一個聽過許冠傑唱片,經歷過七十年代的香港人,總可以隨口哼出一兩句當年他紅極一時的旋律來。七十年代,粵語流行曲好旋律中,起碼有二三十首以上,是許氏作品。這是很了不起的成績。比起香港諸賢,或我國前輩,甚至外國名家,這成績都絕對不弱。這種令行家欣羨的創作才華,已可以令他在香港流行曲史上,佔穩一席高位。吳宏文中反覆提出「許冠傑的歌曲是好是壞並不重要(57)」的觀念,久缺說服力。評介流行音樂創作人,而不理作品好壞,如何說得過去?
試拿他的《鬼馬雙星》一聽。(見附録 -頁 203)
歌是中板,節奏不快不慢,輕鬆舒徐,而仍然保留了Rock & Roll「樂與怒」的勁道。錄音技巧是 70 年代最尖端的技術,吸收了 60年代美國Rock band(樂與怒結他樂隊)和「披頭四」(”Beatles”)唱片灌錄結他與鼓的方法,以電結他變音Fuzz作主奏,而鼓的音色經多米高峰處理,低音大鼓特別有結實質感,所以開始的小引已經先聲奪人。許冠傑的歌聲,咬字清脆,有如說話,而唱法有種很平易近人的草根味道,令廣東聽眾聽來份外親切。他在短句逗的時候,加了個很輕的「呀」進去,像「為兩餐乜都肯制(呀)前世」,「做老千梗好搵過(呀)皇帝」或「贏輸冇時定」句中加個「都」字。這是很典型的粵曲唱法,但因為整套聲音(total sound)的感覺是現代,摩登的,所以只覺得他唱得親切,而不覺得他「土」。朱耀偉所謂「腐朽化神奇」,在這些轉折的險位中,可得明証。因為稍有不慎,尺寸把握得差了半分,就變成與鄭錦昌等人的演繹全無分別。他的獨唱部份在 AABA 的 B 段 , 加了雙軌收音(double tracking)(58)方法來加強效果,也是 70 年代剛剛興起的錄音方法。
歌的電結他承托有度,人聲合唱的襯底和音加得恰到好處,點到即止,是處處有控制的製作。中段電子琴的音色在 70 年代來說新鮮有趣。結尾許冠傑忽然來一句假聲,「唔﹗真係有型咯﹗」令聽眾覺得,阿 Sam 在和他們玩耍﹗於是更添親切。歌曲聽完之後,感覺是開心,輕鬆的,說不定心中還留下一點幽默的笑意讚嘆,讚許冠傑「鬼馬」﹗
整首歌以五音音階為主,但不時加進 fa 音。令他的旋律不是純粹中國味道,親切之中,另有現代城市感覺,正合流行音樂「新中有舊」和「舊中有新」的要求。
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,許冠傑的《鬼馬雙星》,聽的時候,節奏會令聽者忍不住隨強拍拍手和擺動身體。流行音樂有一功用是伴舞。這點,《鬼馬雙星》把握得很準確。即使聽者欣賞此曲的時
候,不一定在跳舞,但輕鬆愉快的喜悅感覺是肯定的,聽一首兩分餘鐘的歌曲,就有這樣的感覺,試問歌迷會不愛許氏的歌曲嗎?
(b) 通俗歌詞.瑕不掩瑜
許冠傑的歌詞,備受注意也備受爭議。可是,沒有人可以否認他擅長捕捉小市民心態。在這方面,他的成就突出,可說成績在香港眾詞家之上。朱耀偉的《香港流行歌詞研究》(59)認為許氏「腐朽化神奇」,並無過譽。他《鬼馬雙星》中段「副歌」的四句歌詞﹕「人生如賭博,贏輸冇時定。贏咗得餐笑,輸光唔駛慶」,短短二十個字,已經把香港人的普遍心態道盡。港人積極、樂觀,但又很有點無奈的拼博精神,就用這寥寥數語中,全部概括,意簡言骸,而且話潑生動,全用口語,平易近人大眾化,真是傑作,足以傲視同群。而另一首《半斤八兩》的電影主題曲﹕「我地呢班打工仔,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」,閒閒一筆,已經勾出香港全部藍領白領人的深心慨歎,功力之深,無法不令人折服。
論者有說他的歌詞「稍嫌粗俗」(60),但許氏歌詞優勝之處,正在其通俗。他描寫的是香港草根階層心聲,用的是這階層慣用的口語詞彙,「賴野」「堅野」「流野」「撈粗野」之類。但為低下階層寫心聲,不用他們的語言,用什麼?難道要把典雅古文寫進去?元周德清《中原音韻》附《作詞十法》,論「造語」,說﹕「造語必俊,用字必熟。太文則迂,不文則俗。文而不文,俗而不俗(61)。」許冠傑筆用白描,俗諺俚語,全不避忌,自然活潑,生機無窮,只教人聽來但覺其趣,不嫌其俗,真是活用俚語的箇中高手,元曲關漢卿以來,未有再如許氏的,真不愧香港詞人中,「俗而不俗」第一人,功力無人可以企及。
他寫社會矛盾,代被壓抑剝削小市民道出心聲。吳宏批評他的歌詞是「傳播學上的 double bind 概念……結果是窒息個人思想發展…..進一步是精神分裂。」和「法蘭克福學派,(The Frankfurt School)的悲觀論調,如出一轍。社會中存在的矛盾,並非許冠傑所製做,文化批評者喜歡「文以載道」,其實除了義正詞嚴之外,又為社會改變了什麼?勇於責人,寬以恕己,豈非更精神分裂?許冠傑的歌詞,其實是真正的香港城市民歌,在經濟起飛的年代,仍然為草根階層市民代言苦況,而用輕鬆生動,笑中有淚的方法出之,所以極為普羅大眾歡迎。
不過,他的情歌作品,寫法反而保守;用字陳舊之餘,連語法也間有不通,寫情寫景寫人,絕少新意。如果將他的「鬼馬」歌曲和他的情歌,放在一起,有時幾乎令人懷疑是兩個不同作者寫的。像《雙星情歌》「曳搖共對輕舟飄」,「曳搖」是因為要配合旋律音調,夾生夾硬把「搖曳」變作「曳搖」,這是粵劇撰曲人急就章通病,不管語言習慣亂來。而「街燈已殘月暗昏」一類前人不知用過多少次的陳言死語,許冠傑時常照用如儀。他還常常有《何時復與卿遊》 (62),《難自禁望君你能見諒》 (63) 一類受傳統粵曲影響的語法,二十世紀七十年代,還用「卿」來稱對方?然後又「君」又「你」,非但「架床疊屋」,而且全沒有時代感,不能不算是瑕疵。但許冠傑受粵劇粵曲影響,可以理解。戰後香港出生的新生代,在處處粵曲聲的環境長大,沒有不受其旋律和歌詞薰陶的。何況,許氏是粵曲世家,令尊令壽都懂粵劇,尊大人更擅奏粵式梵鈴(violin),自小耳濡目染。可是,受影響而至不辨精粗,未免可惜。不過,瑕不掩瑜,許冠傑的「鬼馬」歌曲,為粵語流行曲歌詞,開創了新局面,後來倣傚的人,始終難望其肩背。
(c) 歌聲一般.咬字一流
至於許冠傑歌藝,不是沒有可以議論的地方。他的天生聲線很有個性,但嚴格來說,未算頂好,嗓音不夠圓渾,略有沙啞之弊,尾音收聲時欠滑溜。但唱節奏快的歌曲,咬字功夫,卻是全港歌星中
最頂尖的,字字清楚,直射聽眾耳股,而完全沒有刻意造作的斧鑿痕跡,自然得有如說話,功夫之佳,實在令人忍不住為他喝采。
(d) 製作精緻.態度認真
許冠傑對唱片製作,非常認真和嚴格。他往往花上比別人多數陪的時間去灌錄作品,是精雕細琢的典範。當然,這是超級巨星才享有的奢侈﹕製作預算寬鬆,錄音室和樂師費,視作等閒,務求製作
出精品,不計成本。在一分錢一分貨的「文化工業」製作,許冠傑唱片,當年佔盡優勢。錄音、演奏、混音,全是香港頂尖技術。單說製作水準,未問其他,已知許冠傑唱片為什麼暢銷。
2. 許冠傑其人
(a) 傳奇神話.絕無刻意
論者認為,許冠傑成為香港娛樂界神話,是「文化工業」市場戰略的成功。「他是很理性地(完全是市場規律)將他的聽眾市場分割為適當的segments,而他每一次推出新的歌集就按着各個segment 的需要去編排,務使他的聽眾各適其適(64)。」又說﹕「如果我們着實分析導致我們『喜歡』許冠傑歌曲的每個程序時,我們會發現這樣的一個現象,首先是許的歌曲即將推出,然後是一連串的推廣﹕搞電視特輯,上電台接受訪問,扮鬼扮馬搞新聞之後,整個社會就洋溢着許冠傑,於是我們便喜歡了他,最後付錢。」假如「文化工業」從業員的「市場策略」,可以這樣為所欲為的,這世界一定早已成為奴隸世界。奴隸主是文化工業從業員,支配着我們的一切。當然,「文化工業」不停在推波助瀾,非常努力去「製造」明星。可惜「文化工業」最大的努力和工作,充其量都不外止於推波助瀾而已。文化工業需要吸引消費者,無庸置疑,也無須抨擊。這和社會學家和文化論者寫文章要吸引讀者,目的完全相同。不過,文化工業,特別需要明星。社會學者郭德柯(David Croteau)和海耶斯( William Hoynes ) 在 他 們 合 著 的 《 傳 媒 社 會 》 ( “ Media Society”)一書解釋,明星之所以讓我們處處可見,予人「盤據大眾傳媒」感覺的主要原因,「因為絕大部份傳媒機構的主要經濟目標,是製做『熱門』賣品。」而這些「熱門賣品」(hits),非用明星不可(65)「出版社需要暢銷書;唱片品牌尋找最暢銷四十大金曲與白金唱片;電影製作公司追求破票房紀錄電影。因為大多數的電影、歌曲,和書籍都贃本賠錢,全靠熱門賣品填補損失和製造營利。」一言以蔽之,「明星制度」是多數大眾傳媒機構的運作方法(66)全世界都沒有例外。香港唱片公司運作,當然也相同。
可是,明星卻不是想造就可以製造出來。再多資金,再好的市場戰略,也未必可以泡製出令大眾捧為偶像的超級巨星。明星要有觀眾喜歡的特質,才可以成為明星,超級巨星和熱門文化產品是觀眾和聽眾的喜好製造的。受眾,才是真正的明星締造者。文化研究悲觀論者看不起群眾,誤以為大眾是任人擺佈的無知羊群。又因為群眾教育水平未如這群精英,更增加了他們不自覺的歧視。這裏不妨引述電影奇才奧遜.威爾斯(Orson Welles)的話﹕「觀眾買票來選舉;他們比製造娛樂的任何個人都更具智慧。他們沒有任何事不明白的。唯一難題是如何吸引他們,令他們發生興趣。」(67) 威爾斯1941 年自編自導自演的《大國民》(“Citizen Kane”)在 1998 年美國電影協會「影史上一百部名片」選舉得票最多,成為第一名影片。他也是莎劇名演員,可算精英文化成員。也許他的話,對普及文化悲觀論者看來,不無參考價值。
許冠傑能成為大明星,因為香港人喜歡許冠傑與別不同的特質。他是香港青年人奮鬥成功的典範。大陸來港的窮小孩,蘇屋村廉租屋居民,憑自己努力進入了「香港大學」這最高學府,畢業後加入最新興電視行業,出唱片,破銷量紀錄 (68) 。拍電影,破票房紀錄(69)。開演唱會,又破紀錄。全是港人覺得值得欣羨和應該引以為榮的。這些無花無假的驕人成就,是這位一臉憨態的健康俊俏青年努力和汗水賺回來的﹗不是大眾傳媒亂吹出來的。所以香港人喜歡他,寵縱他。而他也十分潔身自愛,從來沒有負面新聞出現過。大眾傳媒不捧他,還捧誰?許冠傑成為傳奇,成為神話,因為他做了大家做不到的事,得到人人都想得到的成績。
英俊的許冠傑自然在形象上有佔便宜之處。不過,外型和天賦才華一樣,不是想有就有的;既然老天令他有創作才華,又賜他出眾外型,我們何不開心地為他鼓掌?
(b) 樂壇功臣,少人能及
本文作者多年前在許冠傑從歌唱生涯退休的時候,寫過如下的一段話﹕
「整體而論,許冠傑真是粵語流行曲的大功臣,對粵語流行曲的興起,有極大的功績。他是第一位唱粵語流行曲的港大同學。討洋太太,唸洋書的現代青年,也帶頭唱起粵語流行曲來,這實在對粵語歌的推廣,起了極大作用。當時,社會上仍然對粵語流行曲,有很多自卑與偏見。許冠傑是消除這種莫名奇妙語言自卑感的重要人物。在這方面的成就,少人能及。」(70)
今天重讀這段話,覺得完全沒有修正的需要。對粵語流行歌曲的再度興起,許冠傑實在居功厥偉,不可抹煞。
~[註]~
(55)
原刊《理工學生報》第 9 卷 3 期,1980 年 9 月,香港﹕理工學院學生會。載吳俊雄、張志偉編﹕《閱讀香港普及文化 1970 – 2000》(香港﹕牛津大學出版社,2001 年),頁 214 –219。
(56)
宋瑾﹕《關於新音樂美學基礎若干問題的思考》,載劉靖之、李明編﹕《中國新音樂史論集》(香港﹕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,2000 年),頁 78。
(57)
同註(45),頁 217。
(58)
所謂「雙軌雙音」(double tracking)是歌者在另一聲道(track)裡用同音(unison)把旋律重唱,以能與前聲道收錄的全無差異為好。這樣經過混音(mixing)之後重播,就有種加重了獨唱,但卻若有若無的多了二重唱感覺。這是 70 年代剛剛在歐美興起的新方法。
(59)
朱耀偉﹕《香港流行歌詞研究.7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》(香港﹕三聯書店,1998年),頁 61。
(60)
同上註。
(61)
元.周德清﹕《中原音韻》,載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(北京﹕中國戲劇出版社,1980 年),頁 232。
(62)
詞出《獨上西樓》。
(63)
詞出「1982 年十大金曲」《印象》。
(64)
同註(55),頁 216。
(65)
David Croteau & William Hoynes, “Media Society : Industries, Images, and Audiences”, (Thousand Oaks, California : Pine Forge Press, 2000),p.p. 151.
(66)
同上註。
(67)
Frank Brady, “Citizen Welles : A Biography of Orson Welles”, ( London: Hodder and Stoughton, 1990), p.p. 356.
(68)
《鬼馬雙星》1974 年銷量達 15 萬張;1975《天才與白痴》;20 萬張;76 年《半斤八兩》東南亞銷量 35 萬張。後來歌曲被改為日語,並打入日本流行榜。78 年《賣身契》銷 55萬張,盡破東南亞紀錄。
(69)
許氏兄弟領銜主演的《鬼馬雙星》1974 票房 600 萬港元破全港影史紀錄。1976 年的《半斤八兩》,票房 850 萬。
(70)
黃霑﹕《浪蕩人生路﹕人物篇》(香港﹕壹出版,1994 年),頁 29。